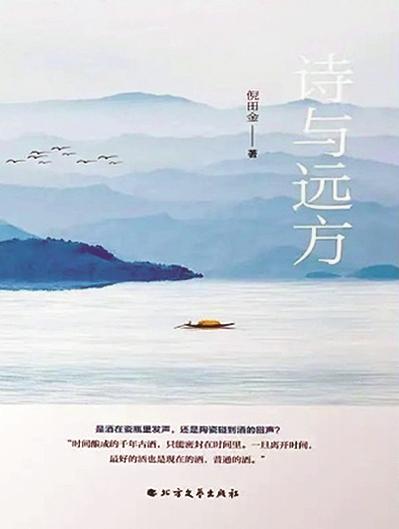陈佳露
倪田金新作《诗与远方》是作者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由《外婆的手杖》《会稽山的芦苇》《红杉林》《越王剑》《太极鱼》等12篇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构成,各自成篇又互相勾连。小说旨在描绘会稽山区人民在改革开放和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深刻变化,以爱情、教育、旅游开发、乡村文化发展等主题为截面,呈现了教育改变命运、求索生命价值和追求个人幸福的乡村故事。
作者以家乡会稽山为地理坐标,在历史纵深与当代精神困境的交会处展开叙事。这座山峦,在华夏文明的漫长蝶变中承载着超乎寻常的使命:大禹在此会盟诸侯、计功封禅,治水功业与政治智慧皆凝固于地名之中;越王勾践于此卧薪尝胆,让“会稽之耻”化作复仇的精神图腾;王羲之在兰亭的曲水流觞间挥就“天下第一行书”,将山水玄思升华为艺术永恒……可以说,故乡不仅仅代表着心的皈依,更是作者创作灵感的源泉。与其说是倪田金选择了会稽山,不如说是会稽山选择了他。
作者以层叠的历史意象为底色,重新审视消费时代下被标签化的“诗与远方”,完成了一场对精神原乡的复归式书写。在《诗与远方》的叙事肌理中,会稽山不是静态的风景,而是诗性回忆和心灵对话的活性肌体。
多少故事发生在会稽山下的溪滩之上。在《外婆的手杖》中,孙国民和卢雪在此定情,走过四月山花烂漫的溪滩;当双方的爱情受到卢雪外婆的“考验”时,溪滩也成了彼此冷静和思考出路的绝佳场所。《会稽山的芦苇》中的杜老师酷爱摄影,他的相机里保存了很多会稽山溪滩的秀丽风景。在小说《遇见》中,校长引进了“我”和阿兰,实现了三人的第一次遇见。在溪滩之上,“我”将心底隐秘的情愫付之于风,守候并见证了阿兰长诗的发表。两人在溪滩上祭奠已逝的校长,让“遇见”迸发出更灿烂的光芒。
细细阅读倪田金的作品,会发现他的文字颇有江南之柔性,而柔性之内又带有芦苇般的坚韧,这便是钟灵毓秀的会稽山所沉淀的特质。在《越王剑》中,亦可窥得其文字的韧性。作者既营造宏大背景,笔锋一转,又在历史回眸处铺陈了一个颇具教育意义的故事,掺杂着人性和诗性。真相在擦拭剑锋的过程中渐渐显露,原来当年学生在操场上挥舞越王剑,本意是想炫耀父亲的珍藏,心念一动,想到体育老师曾经踢过他,最终导致体育老师受伤。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却蕴含着校长的智慧。
在倪田金的作品中,多处呈现他对教育的思考。乡村建设除了发展旅游业,根本上仍要立足教育,这点在小说《爱的教育》中尤为明显。
虽然是一部呈现家乡会稽山风貌的乡村文学,倪田金的创作却跳出了“寻根文学”的窠臼。“密封的瓷瓶里为什么能听到酒晃动的声音?”他在《千年古酒》中的设问,也许是针对读者的,也许是针对这个时代的——这是时间留下的神秘问号。是酒在瓷瓶里发声,还是陶瓷碰到酒的回声?瓷瓶带着千年的回响,反复敲震着会稽山地区人民的内心和灵魂。
当青铜剑、黄酒与溪鱼串联起跨越4000年的精神图谱,我们蓦然发现:所谓“诗与远方”,从来不在他乡的幻境中,而在脚下这片土地的血脉深处,在历史与现实的永恒对话中。每一次对根脉的回望,都是奔向未来的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