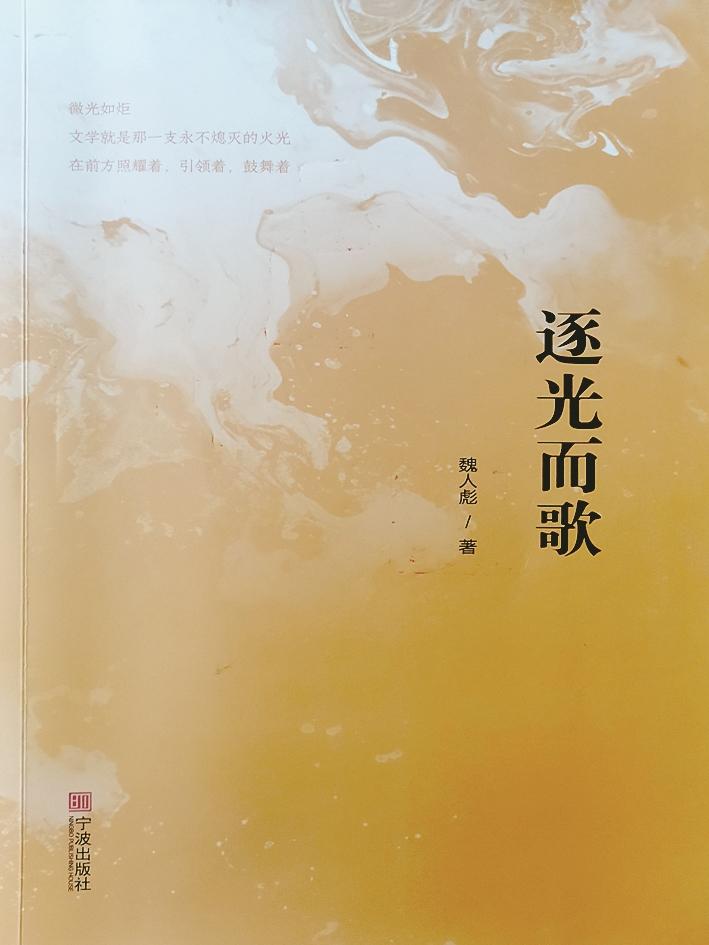杨东标
读魏人彪的散文,让我想起早年他与我一起搞文学的情景。那时候,我还在宁海县文联工作,他在宁海茶厂工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共圆文学之梦。我们办《早春》小报、开笔会、谈作品,一群文学青年聚集在一起,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把县里的文学氛围搞得热火朝天。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我的剧本《明月何时圆》、中篇小说《野鸭滩》定稿本,都是他用工工整整的钢笔字抄写而成的。现在翻出来看看,纸墨泛黄,文学光泽依然温润可感,传递出浓浓的文友情谊。
魏人彪写散文,也写艺术散评,当然写得更多的是散文。一篇一篇地积累起来,便有了早些年出版的《流年中的野蔷薇》和新著《逐光而歌》。书中的篇什,大多在各地报刊上发表过,我也大多读过,现在重新阅读,一个聪颖好学、努力上进的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从青少年到中年,他说:“一件件往事,都是我生命河流中埋藏着的一株株沉香,弥足珍贵,让我在无数个孤寂的深夜里回望,平添温暖。”
《戊己桥畔少年谣》写的是作者年少时在故乡跟表哥捕鱼的故事。“沸腾的潮声中,围猎的喧嚷和呐喊此起彼伏,手电筒的光柱在戊己桥上空狂舞,一段一段的竹帘前,冲不出去的鱼儿一群一群地带着水花蹿出水面,银色的鱼鳞在月辉下闪闪发亮。”灵动活泼的文字记录了他美好童年中的一页。《难忘米酒香》则记叙了他母亲酿酒的过程,“几百斤大米,一笼一笼蒸,把秋夜蒸得越发深沉了”。于是,少年的他便用小碗从塑料布的口子里伸进去,掏出酒酿,偷偷地吃,糯糯的,甜甜的,那种特别的清香,便融进了他后来的文字里。《晒书》《剪报记》《读戏记》《业余编辑》等几篇,可以视作他虔诚地追求学问的生命轨迹。“在书堆边席地而坐,我一本一本哗哗地翻动书页,抖散那些霉味,却不料,也抖出了一串折叠在书页中的往事。”他热衷于剪报,只要是他喜欢的文章,会不厌其烦地剪下来,用糨糊粘贴成一本又一本“剪报集”。不断地翻阅,为他的散文创作注入了另一种营养,也应了“写散文要从做学问开始”之说。他说,受我的影响,也读戏,读我的戏剧作品,读《莎士比亚全集》,读得畅快淋漓,让他无数个夜晚沉浸在美妙的戏剧情景里。他用平实细腻而智慧的文字,记录了他的生命体验,文字承载着那份最本真、最朴实的感动与温情。他的创作态度是认真的,怀着热烈的生命激情及对理想的追求,试图为庸常或不庸常的经历写下文本追忆。这使我想起袁枚那首《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魏人彪的文字功底很好,散文已经写得很娴熟,我希望他有更大的提升,就向他建议,“你不妨写写大散文。”通常所说的大散文,我的理解是指那种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情怀的长篇散文,选准某一题材,从历史、地理、人文、思想、情感等方面多层次地开掘下去,融叙述、描写、议论为一体,洋洋洒洒,不拘一格,率性而文。我曾经在《柔石二十章》中尝试过,成败不计。魏人彪后来调到了宁波市林业局工作,视野一定较先前更开阔了,山林是一个大题材呀,浙东有多少绿地?多少名树?多少稀有品种?里面又有多少民间故事?开掘起来,一定很有趣、很有含金量。
魏人彪思索了良久,回答说:“我做不了。请允许我胸无大志,请允许我小打小闹,请允许我停滞不前。”
当然,其中包含了他的自谦。他的深层想法是什么?《逐光而歌》后记中有一段他与妻子的对话。妻子问他:“你有爱好吗?”他说:“我爱好文学呀。”妻子说:“那不能算。”他问:“为什么?”妻子说:“爱好是平常人琐碎的一种闲情逸致,而文学是你的事业,与钓鱼养花之类不一样。”知夫莫如妻。妻子知根知底的诠释,魏人彪认了。他承认,他对写作是极其认真的,是不计昼夜、不计报酬、不计得失的,谓之“事业”,是准确的。于是,他在后记末尾洒脱地说,“我依然愿意怀揣无限期许爱好文学,把它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沉醉在文字那勾魂摄魄的万千风情和魅力中。我无意成为‘光’,也终究成不了‘光’,我的期望是追随光,与光共舞。”
把文学当作事业,毕一生而追求,书写自己的生命轨迹,何论散文大小?有这一点,就够了。我写下数言,与他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