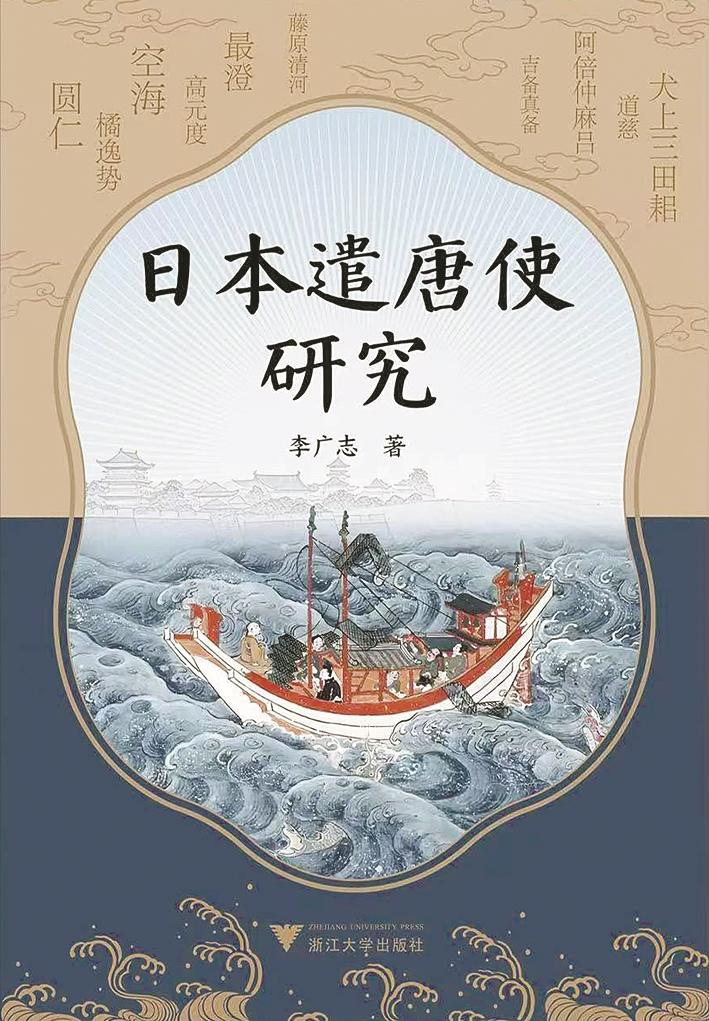斯玉梅
读完李广志新著《日本遣唐使研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的眼前是千年前的骇浪惊涛。历史往往只有深度触摸,才能感知它的温度,才能了解在当时情境下的人物、事件。
从630年至894年,日本派出了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中止,实际成行16次。这16次中就有7次遇险,或舟覆人亡,或因船漂至南海岛屿、安南等地遭当地人攻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据统计,日本派出的遣唐使约5200人次,而其中遇难者起码在千人以上。在没有动力的帆船时代,只有熟练掌握季风、洋流,才能到达目的地。入唐面临如此高的风险,不禁令人瞠目。
遣唐使出发前,日本朝廷会举办一系列的仪式。其中之一是设送别宴,宴上要求五位以上官员每人作一首诗。为遣唐使作送别诗,自奈良时代就已开始,到了平安时代,作送别诗已成为上层贵族的普遍礼仪。
为了让留学人员在中国期间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购买书籍、文物并带回日本,日本朝廷往往给予他们大量的资助,因此留学人员回日本时常会携带大量佛教经卷、儒家经典等文献典籍,日本由此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
在16次遣唐使之行中,有3次与明州有关。分别是第4次(659年)、第12次(752年)和第18次(803年至804年)。第4次本来走北线(山东半岛登州一带登陆),不料第二船漂至越州余姚县,于是返程也从余姚出发。第12次共4船约500人,来程顺利,在明州登陆,回程从苏州黄泗浦出发,遇险。首船漂泊至安南驩州,著名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乘此船。全船180多人,刚一靠岸便遭当地人劫杀,仅幸存10余人,阿倍仲麻吕幸免于难。“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好友李白误以为阿倍仲麻吕遇难,悲痛万分,还专门写了悼念诗。而阿倍仲麻吕从苏州出发时的诗作,在日本被冠以《明州望月》之题,成为日本和歌史上的杰作。其余各船顺利返回日本,鉴真和尚就是在此次搭乘行动中成功东渡日本。
第18批遣唐使在福州长溪和明州鄮县登陆,后从明州返航。803年4月14日,遣唐使共4船从日本难波津出发,不久遭暴风骤雨,沉溺者无数,航行被迫终止。再次出发是第二年春天。第一船于8月10日抵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以南海口(今霞浦县赤岸村)。第二船于7月抵达明州界。第三船去向不明,全船140人遇难。第四船抵达和回国时间晚一年,在唐的靠岸地点不详。
第18次遣唐使成果显著,茶叶在日本的传播、日本新兴佛教的流传,都可归功于它。而随此次遣唐使入唐、返程的日本僧人最澄、空海,都是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
最澄入唐的主要目的是去天台山求法。唐贞元二十年(804年)7月入唐,次年5月回国。最澄在唐的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浙江的明州、台州、越州。最澄前往天台山求法,明州地方政府为其出具的文牒保存至今,已成为日本国宝,被称为《传教大师入唐牒》。最澄在唐接受了天台宗、密宗、禅宗及大乘戒法的传授,归国时带回经书章疏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回日本后开创了日本天台宗。2011年7月11日,在宁波观宗讲寺举行了“最澄入唐上岸圣迹碑”揭碑仪式。观宗讲寺是天台宗的重要传播基地,在此地立碑,以示纪念。
空海的留学计划原定是20年。在长安留学的空海,在青龙寺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即密宗高僧惠果。惠果传法已毕,临终前嘱托空海,尽早回国,将密宗传之东国。大约一年后,遣唐使第四船成员来到长安,空海提出回国请求,获准后提前回国。
空海从明州回国,还衍生出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为寻求在日本传授密宗的圣地,空海在明州海边投掷密宗法器“三钴杵”。回国后,他四处寻找,发现三钴杵落到了高野山的一棵松树上。此后,这棵松树被称作“三钴之松”,广受人们膜拜。空海成为日本真言密宗之祖,高野山也就成了真言密宗的道场。
当最后一次(即第19次)抵达的遣唐使返航后,日本与唐朝廷间几乎不再往来,但彼此的民间交往并没有中断。这期间,海上贸易商团开始崛起,于是日本官员和僧侣,搭乘贸易船只频繁往来于两国。
而明州州治自821年迁至三江口后,建子城,筑罗城,三江口桅樯林立,标志着太平洋西岸的明州港正式建成,并跻身唐代四大港口之列。相比9世纪之前的单一模式,东亚海域出现了跨国贸易繁盛的新气象。
日本遣唐使研究,是一项多领域、跨学科的综合项目,既需要深入掌握中国史、唐史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具备日本史、语言学等方面的专业素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广志副教授完成的《日本遣唐使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文献学、考古学等最新成果,以实证的方法,对中外史料进行了新的鉴别和梳理,系统地研究了遣唐使的全过程。本书共14章近50万字,填补了国内在日本遣唐使研究领域长期以来缺少系统完整研究著作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