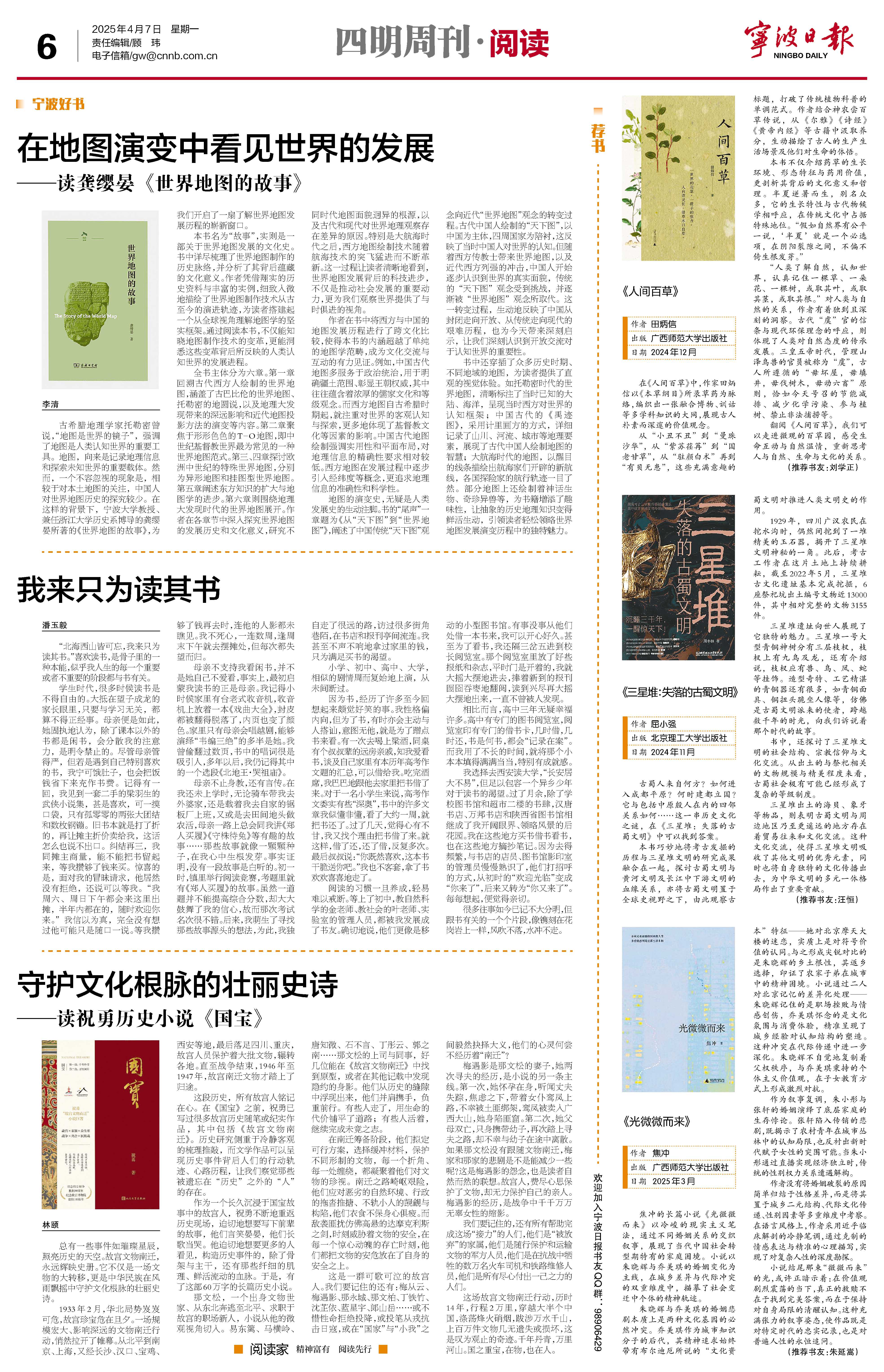潘玉毅
“北海西山皆可忘,我来只为读其书。”喜欢读书,是骨子里的一种本能,似乎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或者不重要的阶段都与书有关。
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读书是不得自由的。大抵在望子成龙的家长眼里,只要与学习无关,都算不得正经事。母亲便是如此,她固执地认为,除了课本以外的书都是闲书,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是明令禁止的。尽管母亲管得严,但若是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我宁可饿肚子,也会把饭钱省下来充作书费。记得有一回,我见到一套二手的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集,甚是喜欢,可一摸口袋,只有孤零零的两张大团结和数枚钢镚。旧书本就是打了折的,再让摊主折价卖给我,这话怎么也说不出口。纠结再三,我同摊主商量,能不能把书留起来,等我攒够了钱来买。惊喜的是,面对我的冒昧请求,他居然没有拒绝,还说可以等我。“我周六、周日下午都会来这里出摊,半年内都在的,随时欢迎你来。”我信以为真,完全没有想过他可能只是随口一说。等我攒够了钱再去时,连他的人影都未瞧见。我不死心,一连数周,逢周末下午就去摆摊处,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母亲不支持我看闲书,并不是她自己不爱看,事实上,最初启蒙我读书的正是母亲。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台老式收音机,收音机上放着一本《戏曲大全》,封皮都被翻得脱落了,内页也变了颜色。家里只有母亲会唱越剧,能够演绎“韦编三绝”的多半是她。我曾偷翻过数页,书中的唱词很是吸引人,多年以后,我仍记得其中的一个选段《北地王·哭祖庙》。
母亲不止身教,还有言传。在我还未上学时,无论骑车带我去外婆家,还是载着我去自家的锯板厂上班,又或是去田间地头做农活,母亲一路上总会同我讲《郑人买履》《守株待兔》等有趣的故事……那些故事就像一颗颗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事实证明,没有一段故事是白听的。初一时,镇里举行阅读竞赛,考题里就有《郑人买履》的故事。虽然一道题并不能提高综合分数,却大大鼓舞了我的信心,故而那次考试名次很不错。后来,我萌生了寻找那些故事源头的想法,为此,我独自走了很远的路,访过很多街角巷陌,在书店和报刊亭间流连。我甚至不声不响地拿过家里的钱,只为满足买书的渴望。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相似的剧情周而复始地上演,从未间断过。
因为书,经历了许多至今回想起来颇觉好笑的事。我性格偏内向,但为了书,有时亦会主动与人搭讪,意图无他,就是为了蹭点书来看。有一次去喝上梁酒,同桌有个叔叔辈的远房亲戚,知我爱看书,谈及自己家里有本历年高考作文题的汇总,可以借给我。吃完酒席,我巴巴地跟他去家里把书借了来。对于一名小学生来说,高考作文委实有些“深奥”,书中的许多文章我似懂非懂,看了大约一周,就把书还了。过了几天,觉得心有不甘,我又找个理由把书借了来。就这样,借了还,还了借,反复多次。最后叔叔说:“你既然喜欢,这本书干脆送你吧。”我也不客套,拿了书欢欢喜喜地走了。
阅读的习惯一旦养成,轻易难以戒断。等上了初中,教自然科学的金老师、教社会的叶老师、实验室的管理人员,都被我发展成了书友。确切地说,他们更像是移动的小型图书馆。有事没事从他们处借一本书来,我可以开心好久。甚至为了看书,我还隔三岔五进到校长阅览室。那个阅览室里放了好些报纸和杂志,平时门是开着的,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去,捧着新到的报刊囫囵吞枣地翻阅,读到兴尽再大摇大摆地出来,一直不曾被人发现。
相比而言,高中三年无疑幸福许多。高中有专门的图书阅览室,阅览室印有专门的借书卡,几时借,几时还,书是何书,都会“记录在案”。而我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将那个小本本填得满满当当,特别有成就感。
我选择去西安读大学,“长安居大不易”,但足以包容一个异乡少年对于读书的渴望。过了月余,除了学校图书馆和超市二楼的书肆,汉唐书店、万邦书店和陕西省图书馆相继成了我开阔眼界、领略风景的后花园。我在这些地方买书借书看书,也在这些地方摘抄笔记。因为去得频繁,与书店的店员、图书馆影印室的管理员慢慢熟识了,他们打招呼的方式,从初时的“欢迎光临”变成“你来了”,后来又转为“你又来了”。每每想起,便觉得亲切。
很多往事如今已记不大分明,但跟书有关的一个个片段,像镌刻在花岗岩上一样,风吹不落,水冲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