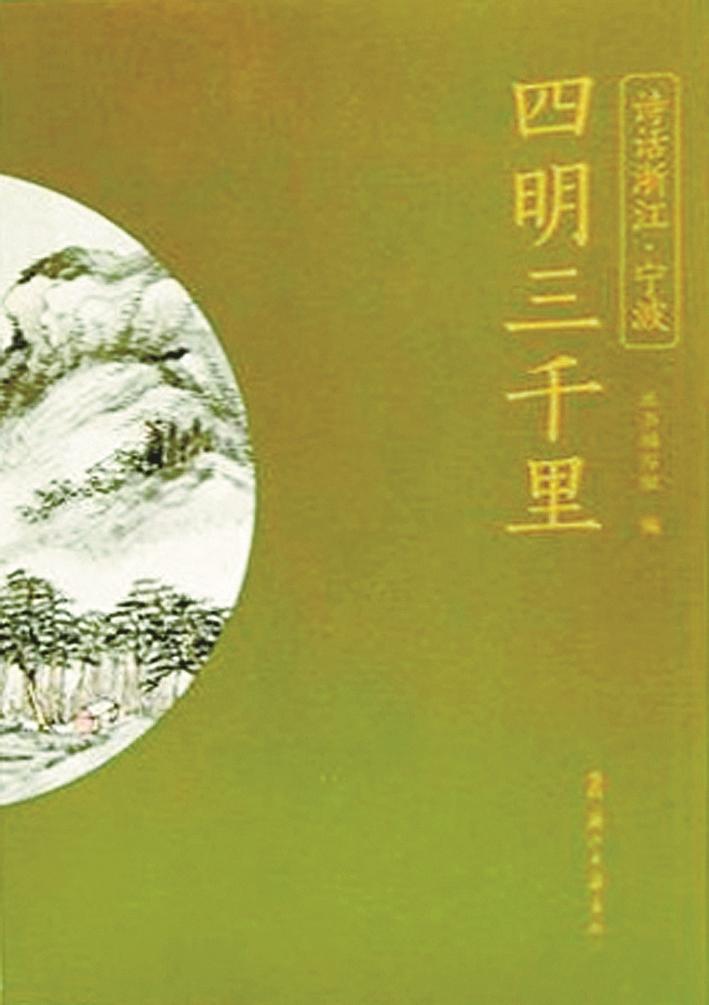袁志坚
前贤纂辑的宁波诗歌总集,如《甬上耆旧诗》《续甬上耆旧诗》《四明清诗略》《四明清诗续略》等,一方面显示宁波是诗歌高地,佳作迭出,另一方面表明宁波诗歌史与地方史的交织,诗史互证。数量可观的宁波古诗词不仅蓄积了前人的生命情感、人格修养和气度襟怀,而且建构了宁波人文地理的维度、场域和格局:海陆山河,如筋骨气血,成为宁波古诗词的常见意象、不竭题材和文化语境、精神载体。
发掘现存文献,可以得知宁波古诗词的地理坐标、人文坐标,以四明山为首。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云:“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浙东唐诗之路,由钱塘而会稽,至四明、天台,接括苍、雁荡,剡中溪、四窗岩、谢公屐、天姥梦,从东晋到大唐,这些符号积淀为文学史、文化史的标识。李白《早望海霞边》前四句云:“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所咏海山奇迹、日月光华,超凡脱俗。《四明三千里·诗话浙江(宁波卷)》一书所选唐诗以四明山为题材者不少,多为游仙之作、烟霞之歌,虽然诗意有些狭窄,但描绘四明山水极具表现力和想象力,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句。
北宋以后,宁波文教兴起,经济繁荣,以王安石知鄞县为转折点,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活跃互动。来宁波为官的文人、由外地迁居明州的氏族,留下了不少诗词作品,本地诗人群体也渐成规模。宋人诗词题材广泛,内容笃实,意象鲜活,笔墨细微,多了生活气息,多了常理、禅趣。除却丹山赤水、深林绝顶,诗人更多着墨于山野田家、清溪古寺,天童山、育王岭、金峨岭、大梅山、雪窦山、五磊山、龙泉山,都留下诗人行踪。
两宋宁波诗词的地标中,月湖尤其夺目。唐代王元暐修它山堰,堰成,引水入城,注月湖。宋嘉祐年间,钱公辅疏浚月湖,筑堤植木,于湖中建众乐亭。以众乐亭为诗题,钱公辅、吴中复、司马光、王安石等诸多文官抒发与民共乐的情感,众乐亭由此成为月湖最初的人文景点。宋元祐年间,刘埕重修水利,筑月湖十洲,并作《咏西湖十洲》组诗,引来友声不辍,酬和连绵。月湖成为人文之湖,实以诗歌为先导,为基调。月湖是诗意栖居之所,簪缨诗礼之族迁居月湖之畔,第院、别墅、书楼、讲堂、驿馆、会所,形成错落布局的园林建筑和人文空间。城市造境、闹处寻幽,无疑在审美趣味上迥异于郊野田居、平芜眺远。舒亶罢职归里,卜居月湖筑“懒堂”,虽然感慨“空令志士泣霜毛”,但士大夫未免难舍“十洲风籁韵笙箫”的风雅。史浩得到孝宗赏赐,在竹洲建“真隐观”,命名“四明洞天”仙境,迷恋的依旧是“玉楼朱阁,冰帘卷起,无限红妆”。不过,世家望族尊学重教值得嘉许,两宋时期楼异的昼锦堂、楼钥的攻媿斋、史守之的碧沚亭、郑清之的安晚园、王应麟的汲古堂,书香盈溢,觞咏不断,对文化的蕴蓄、播衍与传承起到了特殊作用。明代黄润玉建鄞城草堂,丰坊建碧沚园,张时彻建月湖精舍,范钦建天一阁,沈一贯建畅园,清代范光文建天一阁园,全祖望建五桂堂,徐时栋建烟雨楼,继斯文以载道,常吟咏以肆志。如范钦《初秋湖阁》记述了“心远久疏还阙梦,年丰初给买书钱”之喜悦,全祖望在《久不登天一阁,偶过有感》诗中感喟“老我尚知孤竹路,谁来津逮共乘槎”,这是对文化传承的矢志不移。由宋元至明清,吟咏月湖风光、风物、风俗的诗歌数以千计,愈见平易清新。
湖,是大地之眼,也是诗歌之眼。月湖之外,还有东钱湖、广德湖、慈湖、杜湖、白湖、上林湖等,在诗人的笔下,湖光流盼,湖语能言。元代袁士元赞叹:“尽说西湖足胜游,东湖谁信更清幽”,以“清幽”概括东钱湖之魂,千古信然。元代杜国英的诗句“当时不立庸田法,几作农畴种稻禾”,则以宋徽宗采纳楼异之奏请而废广德湖为借鉴,庆幸元代庸田使未重蹈覆辙,东钱湖依然“十八里来平似镜,两三船去小于梭”。写慈湖的诗中,明末刘振之的“亭虚山易入,野旷鹊忘归”,形象表达了南宋“慈湖先生”杨简“物物皆吾体,心心是我思”所主张的本心状态与天机趣味。宋代谢景初《寻余姚上林湖山》中的“平湖瞰其中,翠巘围四垠”,清代叶元垲《杜湖远眺》中的“模糊几点树头屋,欸乃一声山脚船”,清代邵晋涵《白湖竹枝词》中的“梅子熟时看播谷,楝花开后听缲丝”,写景状物,既亲近自然,又体贴人情。
海,是宁波古诗词中独特的地理元素和人文对象。观潮感怀,向海放歌,诗人的视野和格局显然不囿于当下而跳脱出小我。宋代楼钥登育王山,望海明理,“是中始觉宇宙大,眼力虽穷了无碍”。沧海空阔,启人心智。元代张翥在招宝山望海,所见“只是天是水,无地无山”,故而“长啸壮怀宽”,抛却俗虑,襟怀坦荡。明代戚继光艰苦抗倭,回首龙山之战,感慨“曾于山下挥长戟”“遥看沧海舒孤啸”。文天祥《乱礁洋》诗写于抗元途中,乱礁洋在象山县东北,诗人亲睹“云气东南密,龙腾上碧空”而振作精神,“孤愤愁绝中,为之心广目明”。王阳明避祸泛海,突遇风暴,却镇定自若,“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悟得“吾心自有光明月”之境界。清初张裴《东海打鱼歌》,既有“春海茫茫鱼起口,渔人千帆出海走”之赞叹,又有“不见公家赋税频,簿书不遗鬐与鳞”之抨击。清末八指头陀《登太白峰绝顶眺海》诗成于《辛丑条约》之后,“河山北望情何极,鲸浪谁能靖五洲”,字字激昂,抒发了对列强侵华的愤慨、对社稷安危的忧虑。这些诗歌,或气势磅礴,或气骨峥嵘,或气魄雄强,催人向上。
在山海之间流淌的姚江,堪称明清思想史的坐标,阳明心学、浙东史学以姚江为发源地,蜚声海内外。王阳明游杖锡不忘感愤时事,“探幽冀累息,愤时翻意惨。拯援才已疏,栖迟心益眷”,以人心为大道,以担当为信念。黄宗羲抗清失败避居化安山,“锋镝牢囚取决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意志如磐,希望不灭。张苍水被清军押往杭州经过家乡时以诗辞别父老,“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敢于牺牲、永不言弃的精神可昭日月。黄宗羲送万斯同北上纂修《明史》,“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谆谆嘱托如金石之声。全祖望重定黄氏《留书》,向先生致敬,又担忧师道之不传,“犹闻老眼盼大壮,岂料余生终明夷。畴昔薪传贻甬上,而今高第亦陵迟”,何其沉郁愤激!姚江诗章,经史如铭,家国为重,摒弃机巧,唯见赤诚。
宁波古诗词中,以风物、特产为题材的比比皆是。写越窑秘色瓷器,唐代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和徐夤“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堪为名句。宋末元初的诗人戴表元久居剡源,喜以家乡风物入诗。写制藤纸,“剡人伐藤就溪洗,匠出素笺黄土纹。大笺敷腴便竿牍,小笺轻盈日千束。”又写焙茶,“山深不见焙茶人,霜日清妍树树春。最有风情是岩水,味甘如乳色如银。”写东海海鲜的诗也不少,如宋代舒亶的“抵虎螯经夏,跳沙蛤趁潮”,宋代谢翱的“盆中蓄海石,左顾如牡蛎”,明代屠隆的“五月黄鱼熟,千帆劈浪过”,明代吕时的“香多吸老酒,鲜极破黄鱼”,青蟹、蛤蜊、牡蛎、黄鱼,活色生香。
宁波是大运河的入海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以上写风物、特产、经济之诗,皆可证此河海交汇之城的经济史、社会史。关于宁波的“海丝文化”,在《四明三千里·诗话浙江(宁波卷)》所选诗词中,有不少例证。如南宋陆游《明州》诗中有“海东估客初登岸,云北山僧远入城”之句,当时,日本、高丽行商来明州做生意已属寻常事。南宋亡后,临济宗高僧无学祖元东渡传法,成为日本禅宗佛光派始祖,天童寺外的宿鹭亭是他启程赴日之首驿,故而《怀太白》诗寄托了“夜静不知沧海阔,几随宿鹭下烟矶”之乡思。元代程端学有《赠安当之同年归高丽》诗,如诗题所言,高丽人安当之与程端学于泰定元年同中进士,这首诗见证了中国与高丽的政治文化交往。元代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诗中有“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的叙述,可见宁波市舶贸易之繁荣。清代晚期,日本友人冈千仞写下《登宁波天封塔》诗,“鳞次甍瓦陶猗屋,林立帆樯欧米舟”之句,描述了开埠后的宁波景象,同时他有感于当时列强侵华形势,发出“澄清谁抱中原略,极目苍茫海日收”的喟叹,希望中国振兴图强,海晏河清。在长期的对外交流中,宁波文化形成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质。
搜罗、汇集宁波历代诗词作品,有利于还原历史、梳理文脉、倡导诗教、振奋精神。今天,编选《四明三千里·诗话浙江(宁波卷)》,实乃前人传统之赓续,且由此可振叶寻根、溯源析流,乃至入古出新、返本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