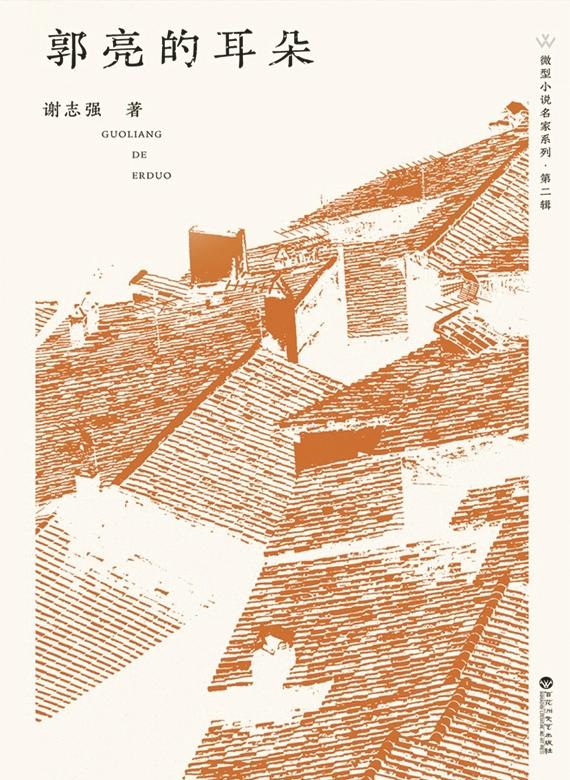蒋静波
谢志强有一副好听的嗓音,普通话里带着乡音。无论是听他的文学讲座,还是读他的作品,最终,一切仿佛都化作了他的声音,在耳畔反复响起。
《郭亮的耳朵》是谢志强最新出版的微型小说集,收录的作品均属“徐州笔记”系列,所写皆为徐州往事。这些故事的素材由两部分构成:徐州籍同学寄来的地方资料和小时候听徐州籍同学的父母讲述的往事。面对这些素材,谢志强以文学的形式发声,来讲述那片土地上尘封的故事。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备忘录》中指出,利用库存资源是未来文学的趋势之一,而谢志强正是此道的践行者。几十年来,他潜心收藏古今中外的童话、民间传说及地方史料,并以此创作了《黑蝴蝶》《过手》《珠子的舞蹈》《江南聊斋》《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等作品。这种方法,他称其为“重述”。
这令我联想到西班牙作家阿莫多瓦的微型小说《信》。母亲为邻居读信、写信,“我”却发现母亲念出的内容与信上写的并不完全一致。她会依据生活的逻辑,虚构一些细节,如“外孙女想念外婆用装满水的盆在家的前门给她洗头”——其实信里根本没有提到外婆。她念完后,大家都很高兴。这位母亲的“发声”,早已超越复述,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层面——这正是谢志强所说的“重述”。
重述,就像把东西吃进去,化为内在的营养,通过有声音的文字表达出来。重述有两种,一种是对史料的重述,还有一种就是对经典的重述。
对于前者,有人简单地认为,重述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言把资料再讲一遍,实则不然。文学创作承载文化记忆,根植于历史土壤,重述尤其如此。它如同“戴着镣铐的舞蹈”:史实是土壤,记忆是根系,重述则是生长出的枝叶。它无法脱离根本,却能摇曳、变色,发出沙沙的声音。
重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注入新意,用发现的眼光跳出固有印象,发掘他人未曾留意之处。在首篇《花卉40盆》中,张勋复辟时以电报“花卉40盆”为暗号,要求心腹张文生调动40个营的兵力赴京支援。而张文生却真的送去花卉40盆,按兵不动。在这一史实基础上,作者虚构了邻居朱翁这个角色。朱翁如同穿起珠子的线:张文生贫困潦倒时,他付船费,助他过湖当兵;张文生从军后,他四处宣扬,引起张勋注意,让张文生渐成其心腹;张文生收到电报时,又是朱翁听他袒露心声……从张文生对朱翁的厚报和信赖中,读者看到了一个知恩图报的人物形象。张文生拒绝出兵,说:“40个营的兵力,也是肉包子打狗,成不了事,当个兵,不容易呀。”作者在重述中,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改变了张文生“观望风向”或“背主求荣”的固有形象,赋予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时完成了小说核心的升华。
重述的力量,在于细节的铺陈与运行。在《娘,我睡哪一头》一文中,作者避开对惨剧的正面描写,只提取母子被推入土坑前的瞬间场景,面对陌生的土坑与凶恶的敌人,刚学会说话的弟弟问:“娘,我睡哪头?”此问以孩童的天真反衬出极致的残酷。同时,“枪”的意象作为另一条暗线贯穿全篇:神枪手父亲弹尽牺牲;弟弟被埋前,敌人夺走了他怀揣的父亲做的小木枪;哥哥最终继承了弟弟的木枪和父亲的真手枪,并打响了父亲的枪,到母亲和弟弟墓前告慰。在重述过程中,作者强化这些细节,串联起牺牲、传承与告慰,使故事重心转移,立意和境界也随之深化。
本书分为《郭亮的耳朵》与《过河说话》两辑。如果说第一辑主要依据官方史料创作,其方法是“能走,即写实”;那么第二辑则更多基于个人的记忆,其方法便是“会飞,即幻想”。在第二辑中,作者摆脱了史料的束缚,直接展翅飞翔。
在《听见麦子叫唤的小男孩》一文中,兜兜既能听见麦子的“叫唤”,也懂鸟语。他多次提醒爹娘:“麦子呼唤,要割麦。”爹娘对其所言选择了相信,从而躲过了冰雹灾害,而不信者则损失惨重。万物有灵,孩子的纯真连通着自然与人类,只是成人早已关闭了心灵的通道。这是作者对成人灵魂的深切提醒。
书以《郭亮的耳朵》为名,本身便是一个精妙的文学隐喻。它源自书中的同名作品,主人公郭亮耳力非凡,能在银圆跌落的喧响中,精准辨识其真伪。谢志强在后记中坦言:“我自以为拥有一双‘郭亮的耳朵’。文学需要这样的耳朵。”
他正是用这双“文学的耳朵”,聆听历史的低语、土地的呼吸与童年的回声,完成了一次次深刻的重述。而作为读者,我们翻开这本书,不也正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另一个能够聆听文学之声的“郭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