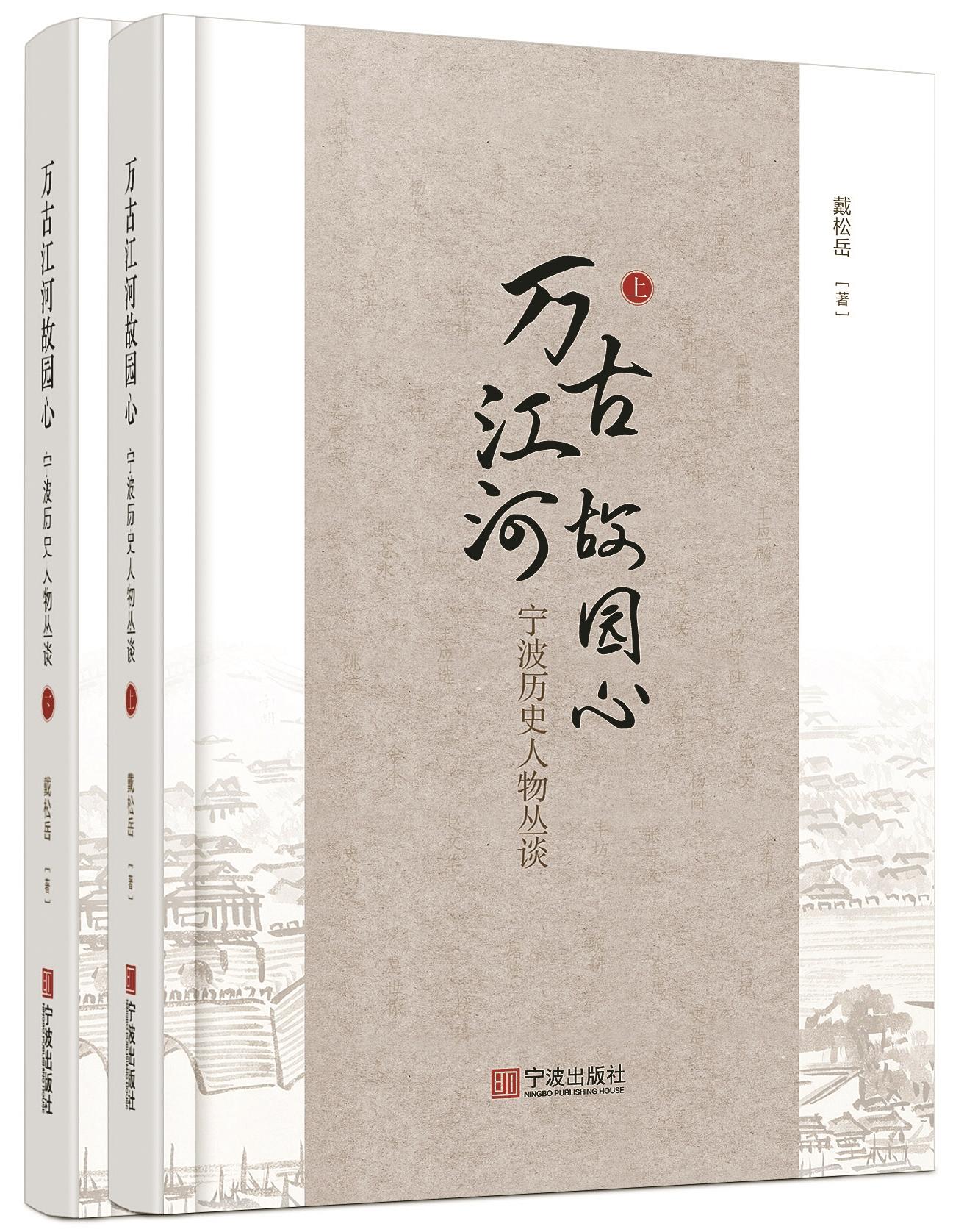赵淑萍
戴松岳的新著《万古江河故园心》,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史学积累与文化思考。全书以六七十位宁波历史人物的评传为主线,同时辅以对姚江文化、慈城慈孝文化、鄞州文化、宁波商帮文化的特征与人物群体性格的剖析。这不仅是对这片土地历史的深情回溯,更是对本土精神的深刻挖掘。读完全书,你会感到,这不仅是一部宁波地方人物史的汇编,更是一部凝聚着温度与文化情怀的精神志书。它在有限的篇幅中横贯千年历史,在史实叙述与文学书写之间找到了极富张力的平衡点,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史识与独特的才情。
戴松岳写就了一部群像式的历史人物评传。他笔下的宁波人物跨越千年,有名臣、志士、才俊。有的彪炳史册世人皆知,如王应麟、张苍水、全祖望等;也有的被尘封在史册角落不为人晓,如追随方孝孺殉道的戴德彝、大明遗民周容、抗倭英雄蒋洲等。
作者用现代人的视野重新审视古人,为那些被时光湮没的生命赋予新的光彩。例如,他对舒亶的评价就与传统认知大相径庭。在许多历史记载中,舒亶被视作北宋时期的一位权臣,甚至被贴上“奸佞”的标签。但戴松岳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和多角度分析,从文学史与政治生态双重视角出发,指出舒亶在政治上的复杂性及其对变法的实际贡献。而对赵文华的描述,更具颠覆意味。作者不是为其“洗白”,而是让读者看到在“奸佞”与“智谋”之间的人性张力——一个在明代政治网中进退维谷,仍怀个人忠诚并对桑梓行善良多的人物。这种再阐释的勇气,源于学者的独立精神,也赋予《万古江河故园心》思想上的锋芒。不拘泥于成见的写作方式,使本书在学术严谨之外,也具备了强烈的思辨性与启发性。
书中对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的书写极具发现意义。譬如,世人皆知方孝孺,但忽略了他的好友、探花戴德彝在“不惧灭九族”的血色背景下,选择了从容赴死。戴妻项氏在夫亡家破之际,烧毁族谱,以身试刑,坚如磐石,最终保下了戴氏族人。又如元曲大家张可久,他的作品常与马致远、乔吉并提,但在本土几乎被人遗忘。李慧娘这个戏曲形象经久不衰,而塑造这一形象的正是明代宁波戏剧家、文学家周朝俊。还有抗清英雄王翊的好友陆宇[火+鼎],在王翊蒙难后,冒死抢下他的首级带回家秘藏,每逢祭日必请出供于案上,然后对着首级痛饮。作者用饱满的笔触,让这些人物从名字变为活生生的灵魂。他们不仅是宁波文化精神谱系中的一环,更是有血有肉、有家国之思、有性情风骨的生命。
戴松岳的文字,既有史家的冷静与坚实,又有文学家的温度与诗意。他精通史料,也善于调动语言的色彩与节奏。在他的笔下,人物往往通过细节入场,文章中时而闪现抒情的句子,时而收束于理性的分析,使作品既有史实支撑的厚重感,又有文学感染的流动感。常让人仿佛置身其间,听到那个时代的声息。这种兼具史学与文学品格的写作,是戴松岳多年功力所至,也与他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深爱文学的历史学者的自觉。以他对宋词大家吴文英的研究为例,耗时35年,写下7万余字,参考近200种文献资料,极尽考证之精审。前半部分是极为专业的词评,作者分析了吴词秾丽而高远的意境、幽艳而凝挚的基调,以及如万花筒般变化组合的意象。后半部分概述了吴词研究的学术成果。这种持久研究与深度钻研,使作品同时具备文学的魅力与学术的权威性。
全书的结构极具纵深,作者在处理点与面的关系时颇见功力。人物是点,时代是面;细节是水流,史识是宽广的河床。每一篇评传都可独立成章,却又在全书的框架中交织成一幅宏阔的宁波文明长卷。他书写人物,不仅关注其个人际遇,还将他们放在时代的坐标系中审视。例如书写宋代人物时,他将其置于全国政治文化格局之中,并描述他们与同时代人物的关系。这种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叙事,使《万古江河故园心》具有“地方书写即国家书写”的意义。戴松岳善用细节穿透时间的壁垒,让人物走出史料的冷寂,成为可以与当下对话的存在。这种“点面结合”的叙事方法,使书的节奏在宏大与细微之间不断转换,既有史学的深刻,又有文学的温润。
辛勤耕耘近四十载,戴松岳的付出终于结出了硕果。如今,他对本土人物如舒亶、史氏人物的重新解读,以及对姚江文化、慈城慈孝文化、鄞州文化、宁波商帮文化的深入论述,已获得学界广泛认可。宁波历史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而这一切的繁荣,离不开像他这样长期专注于史学研究并不懈传播的学者。
《万古江河故园心》的价值,不仅在于史料的丰厚与笔法的精妙,更在于它重新启发我们思考:历史为何要被书写?又该怎样生动展现?在信息快速更迭、文化认同不断被稀释的时代,这部书的问世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在大历史中寻找小人物,在小叙事里感受大文明。宁波的故事,地域的故事,终归指向中国文化深层的灵魂——那是一种历经风雨仍能自我更新的生命力。《万古江河故园心》是一部为宁波立根、为文化立魂的书。它所留存的,不只是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