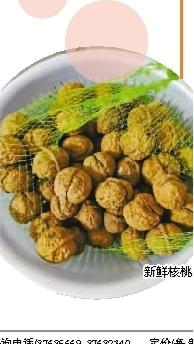“咔嚓”一声,我用小榔头砸开一颗核桃,这熟悉的声音和动作,让我想起了很多往事。
小时候吃的是干核桃,父母认为这是进补之物。到了冬天,帮母亲用小榔头砸核桃,是常事,也是挺大的一件事。大颗的仁放入大碗中,零碎的“小不点”,就直接扔进嘴里了。用小捣臼把好几斤的核桃仁一一砸碎,是很费功夫的。为了吃,我只能忍着。母亲用毛巾包着熟芝麻,将之砸碎,加糖后拌在一起,最后上锅蒸,分两次,每次蒸两个小时才成。所有过程,都是手工完成。
那时候的芝麻,是父亲在旱地上自己种的。奶奶在世的时候,要把核桃芝麻仁在饭镬里蒸7次的,说是这样才“劲道足”。每天让我和姐姐吃上几勺,说是能“奖补”(北仑方言,进补的意思),使人健壮,还能补脑,学习会聪明些,将来好去考大学。母亲有时候还会放冰糖,我每次总比姐姐吃得快一些,吃完了再去偷吃姐姐的那一份。剩下的核桃壳也还有用,可以煮蛋,就是不放茶叶也能煮出那种茶叶蛋的颜色。
第一次吃新鲜的核桃,是大学毕业后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一个小贩推着小推车,在路边贩卖。山东同伴说这是新鲜的核桃,便好奇地买了两斤。小贩帮忙砸开壳,我吃了一个,口感非常生脆,嫩得像初春的嫩笋,一咬下去,满口清甜的汁水。一两天后,随着水分的减少,脆感还在,清甜味还有所增加。
北方的核桃皮有点厚。新疆和云南的纸壳核桃,壳很薄,徒手就能剥开。我去云南旅游时,在泸沽湖畔一家饭店门口见过核桃树,枝叶茂盛,底下可以乘凉。叶子浓绿宽大,为羽状复叶。核桃青果鸡蛋般大小,表皮上有细细的绒毛。我的手指摸过之后,指间留下了淡淡的香味。
后来成了家,核桃从童年的零食,变成了一份牵挂。夫人怀孕的时候,听说核桃能补脑生发。嫌我头发少,怕孩子遗传,于是买了很多核桃回来,每天让我砸上四五个给她生吃。生吃有点腻了,我就到老菜场附近一家店里去买成品,当场加工,还会加上花生米和冰糖。机器加工就很细腻,口感甚佳。算起来,她怀孕期间,吃了几十斤核桃总是有的。女儿出生时,如我们所愿,头发乌黑光亮,非常稠密。现在女儿16岁了,长发披肩,也喜欢吃生核桃和核桃芝麻馅的食物。
今年,同事给了我一小包核桃仁。撕开包装袋,里面是洁白如玉的鲜核桃仁,生脆微甜,回味悠长,让我想起30年前在山东第一次吃到时的情形。于是网购了3斤新鲜核桃,几天后到货,是云南昆明所产。外壳不算厚,但有韧劲,需要工具才能砸开。于是每天砸上四五个,当作水果或零食来吃。据说比较适合我这样成天坐办公室的人吃。
核桃砸得多了,我在一堆壳里,留意到薄薄的木隔膜。上网一查,方知有个好名字,叫“分心木”,是一味中药。《本草再新》里说它能“健脾固肾”,现代人还说它能治疗失眠 。夫人最近睡眠不佳,我找出这些先试试泡茶水有没有效果。
一枚核桃,从青果到仁,再到不起眼的“分心木”,竟无一浪费。我想起奶奶的七蒸之法,母亲的手工捣碾,如今我又挑出这淡褐色的小木片。如此这般物尽其用,或许是关爱之意最朴素的隐喻,它所“奖补”的,何止是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