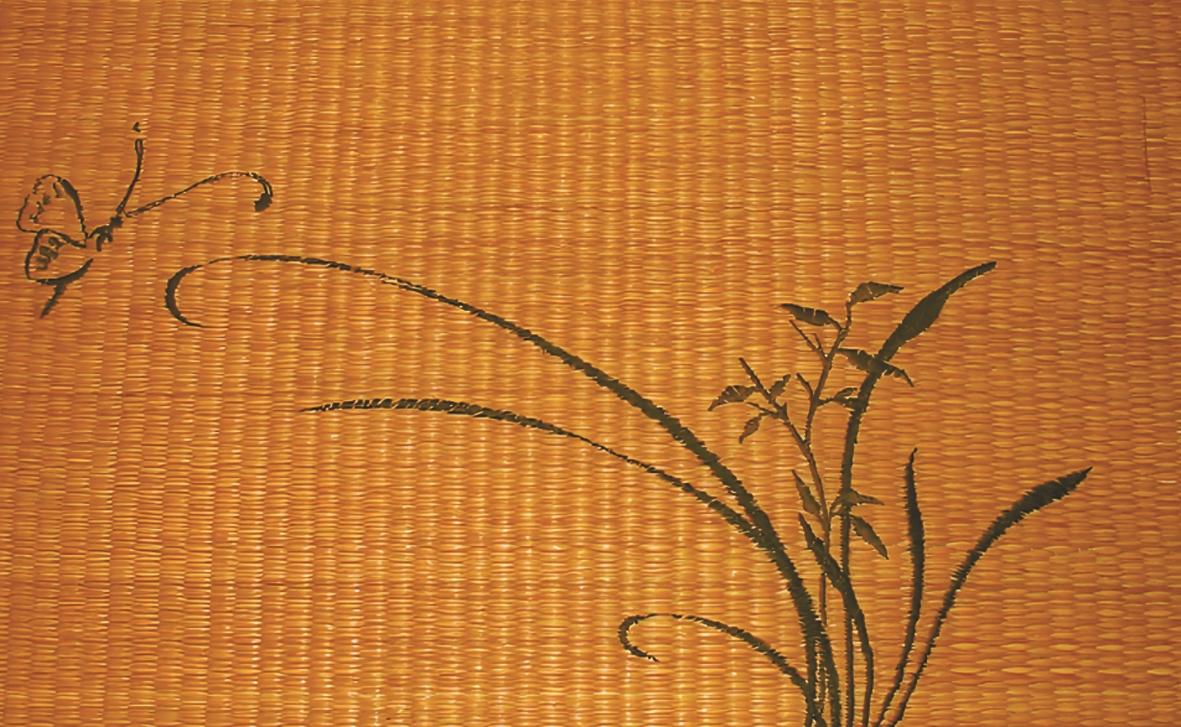□桑木
小时候,夏夜乘凉,大人们边用蒲扇拍打蚊子,边给我们猜谜语。有一个谜语至今仍记得:“出身青草里,搬到卧房中,又见日头又见水,还见鸳鸯配成对。”姐姐轻轻抿笑,眼角微微上扬,她知道谜底,故意不说。我们猜东猜西,没猜准。她才笑着说:“我们每晚睡在什么上面?”我们恍然大悟:蔺草编织的席呀。
我的伯父是村里私塾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他讲起席子的前世今生,故事可多了。什么战国时期的竹席、唐朝的藤席、清乾隆年间的象牙席等,讲得有板有眼。还摇头晃脑背诵白居易的《苦热中寄舒员外》,我们根本听不懂,唯有“藤床铺晚雪,角枕截寒浴”,似懂非懂,觉得那“藤床”一定很凉快吧。伯父说,席子不仅是纳凉的工具,更承载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每一根草、每一缕藤,都经过精心挑选和编织,才成就了这份质朴与清凉。我们听着,仿佛穿越千年,感受到那份悠悠岁月中的宁静与安详。
我们生活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抑制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只知道草席,村里人称它为“滑子”。“滑子”虽简单,却承载着乡村生活的质朴与温情。夏日夜晚,躺在上面,凉意透心,仿佛能听到草叶间的低语,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
上世纪70年代前,宁波人用的席子就是蔺草编织的,大多数是古林草席。以“白麻筋”的为上等货。蔺草编席时,支撑加强的经线采用苎麻或络麻搓成的细绳,柔而韧。密密匝匝的蔺草席,光滑、微微清香,经得起汗渍,有散热的功能。据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早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古林草席已作为特产远销外地。至宋代,草席生产已具相当规模。
1954年,周恩来总理指名古林的“白麻筋”草席作为国礼,赠送给参加日内瓦联合国大会的各国首脑,从此,古林草席饮誉世界。
宁波人席子从小用到老。夏天,婴儿的摇箩上铺有小席子,孩子外出读书、学生意都得自备寝具,席子必不可少。1963年我读初中,那时物质匮乏,购席须证明。我妈到村里开证明,然后到供销社购买。脸盆、热水瓶、席子、衣服、一周吃的大米,都挑在担子里,那席子晃来晃去。步行6公里,到学校气喘吁吁。这席子陪伴我读完了初中,又伴我去更远学校读高中。
以前,村里瓜地搭建的瓜棚中,有简易床,床上只铺一张草席。客人来了,床不够,席子铺地,也是一张床。连老人作古,棺木中也要铺有“材席”。可见宁波人对席子的钟爱。
席子、蚊帐是夏天必备寝具。随着时代变迁,席子的制作材料、工艺也不断精致。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上兴起“麻将凉席”。这种凉席用竹片、牛筋线串起来。因竹片像麻将,故名。此席子相当光滑、凉爽。在空调卧室里应用,更有冰凉之感。记得上世纪九十年末,三峡地区市场上出现一种牛皮凉席,质量好,价位高,是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
随着时代发展,席子种类更多了,各种植物纤维制作的凉席面世:有的正面凉而不冰,背面防滑,还有绑带设计,绑在床的四角,可使席子更平直;有的席子由两张拼接而成,这样易于晾晒和折叠收藏。这次去女儿家,她给我准备的凉席是采用纳米材料做的,像丝绸一样顺滑。席面上绘有雅致图案。我这下乡老太,躺上去恐污了那图案,揩时更是小心翼翼。女儿笑我太小心了,那席还可以放到洗衣机里洗的,打什么要紧。
直到现在,我还是钟情古林草席,它材质天然、纹理平整、顺滑带糙、自带清香,现经科学处理,还不会生席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