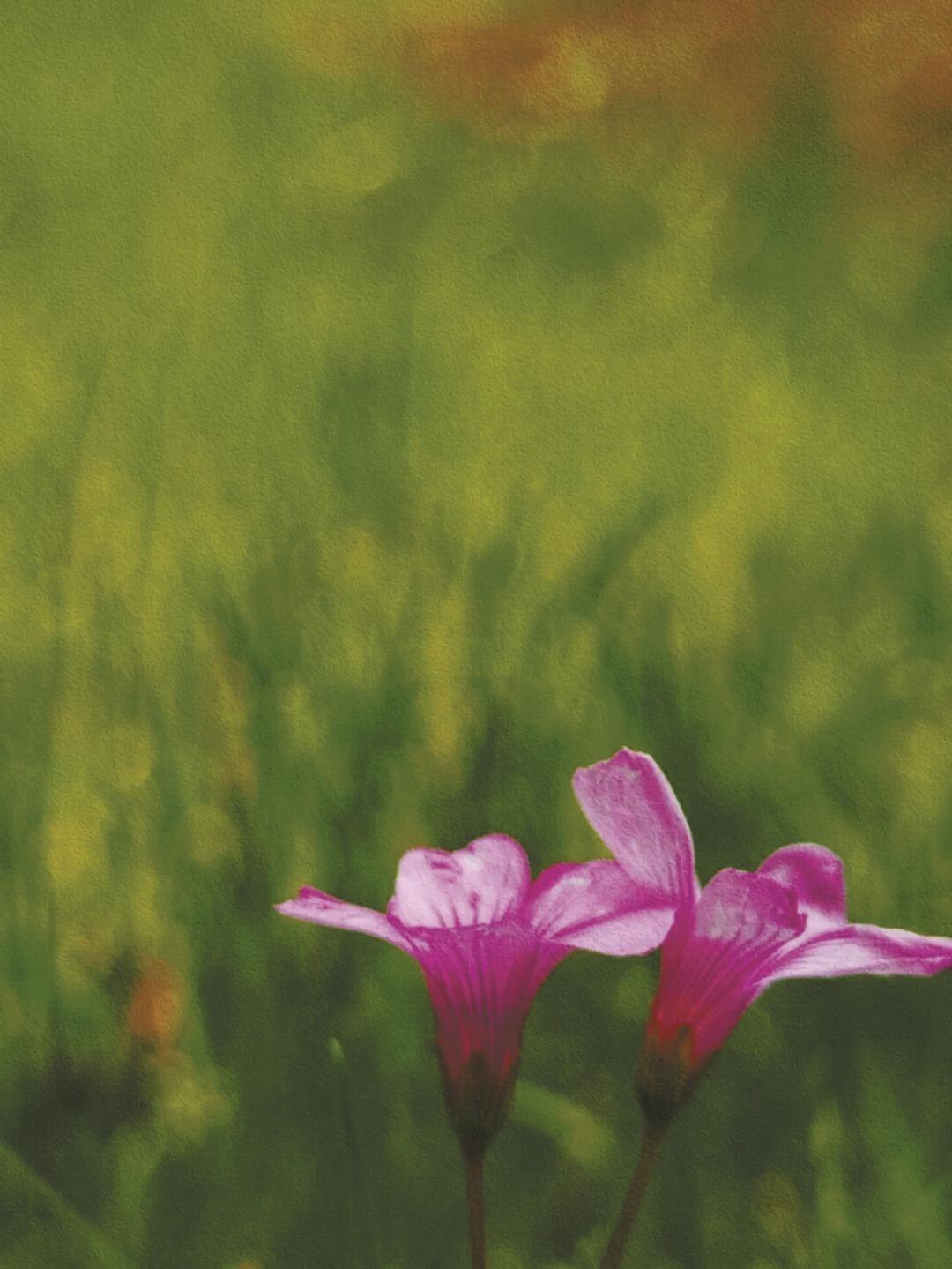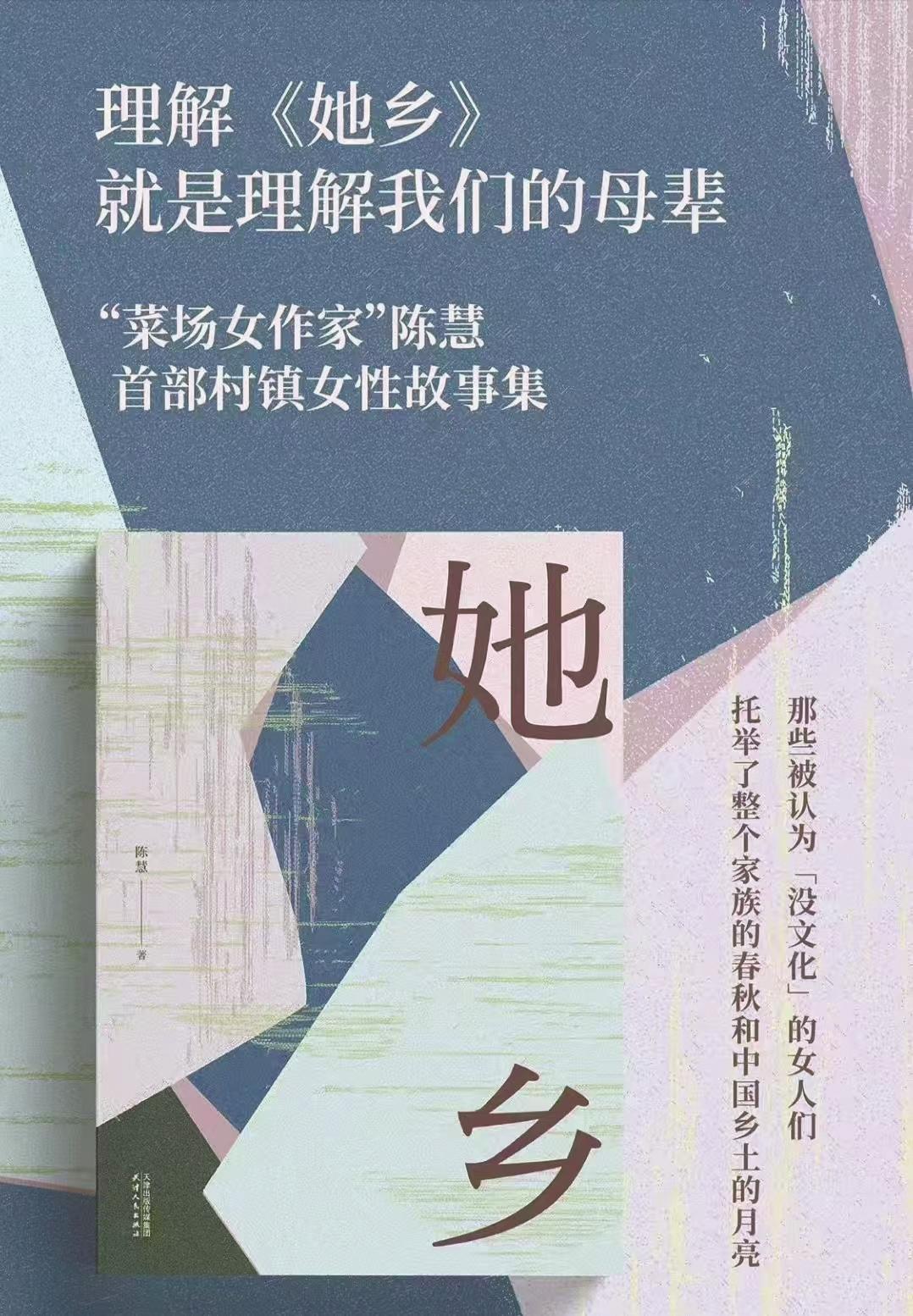《她乡》主人公全是女性,故乡苏北农村的女性和现居地浙东山区的女性。
她们是如此的普通,没有祥林嫂的故事性,也没有李双双的时代性。但陈慧用细腻的笔触让她们进入了文学,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让她们隐秘的疼痛和生活的韧劲被看见。
看到这些女性,我会想到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曹禺笔下的繁漪。尽管时代和身份有天差地别,但令人悲哀的是,她们的疼痛本质是如此的相近。
我们曾把娜拉和繁漪的不自由和傀儡形象归咎于社会不让女性工作,她们没法经济上独立,以致失去了把控自己命运的力量。但《她乡》中的女性基本上不但自食其力,而且承担养儿育女的重任。可在婚姻中,她们照样个个遍体鳞伤。
养母结婚好几年总是怀不上,喝偏方——童子尿,她说:“前后喝了两三个月,喝得我饭也咽不下去了,脖子上瘦得只剩下三根筋,走起路来两条腿软绵绵的。”后来公公婆婆松了口,说领个孩子养,这才不折腾了。
4年后居然怀孕了,但生孩子的时候九死一生。时隔多年,当“我”问起她当时的感受,她说“我忘记了”。但她没有忘记自己的丈夫在医生面前的一跪。因为记着,所以不管后来丈夫有多么荒唐,她都守着这个家。
“她和养父的婚姻更多的时候是她一个人的独自修炼。婚后10年的不孕不育,她要修炼;丈夫沉溺于酒桌,她要修炼;最诛心的是养父此起彼伏的花心事,还是要她修炼。”当年生孩子时的一跪,成了她婚姻的支点。
而母亲和小姨同样也是靠支点维持着婚姻。当“我”离婚后,父亲和小姨父都劝我再找个人。但母亲和小姨的意见恰恰相反,因为她们自己“终其一生都在忍着皮开肉绽的疼痛”。
“父亲在我母亲眼里脾气差,心眼小,不讲理……数落到最后,‘他顾家’,她用力地强调了这一点,脸上满是庆幸。”
“小姨娘很少在我面前说到姨父。一个初秋的雨天,我们相向而坐。她低声地坦承了日子深处里那些点点滴滴的辛酸,泪水悄然落下。擦去眼泪,她依然笑着给我姨父盖上‘特别勤劳’的好人印章。”
这亦真亦假的“庆幸”和“笑”背后其实是善良女性太多的不忍和不得已。“她们习惯于把婚姻的完整性展现给亲朋好友看,并始终认为这是一种责任。”但她们的身体和心灵真切地感到了疼痛,那种岁月带不走的疼痛。
而“我”的婚姻再努力找也找不到支点。《她乡》中的秋囡和阿妮都可以看到“我”的影子。
丈夫形同虚设,和阴晴不定的婆婆同吃同住。“秋囡害怕看到婆婆板着的脸,但除了这个家,她别无去处。每天中午她踏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偷偷打量婆婆的脸;如果没有硬邦邦地板着,她不由得长舒一口气;如果明晃晃地板着,她便下意识地把自己站成一张薄薄的纸,尽量不占据老屋里的任何空间。”
当阿妮提出离婚后,村里的邻居来劝和,“谁的劝,阿妮都不听。她鼓足了勇气从寒冷刺骨的烂泥潭里爬上来,哪怕全世界都站在她的对立面,她也绝不重蹈覆辙。”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人的认知和思维还留在农耕时代,把几千年的偏见当真理,把女性的母性当软肋。女性的疼痛是社会的疼痛,无视这些疼痛,最终必将遭到反噬。时代就算叫不醒周朴园们,但终究会让更多的“她们”更清醒,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