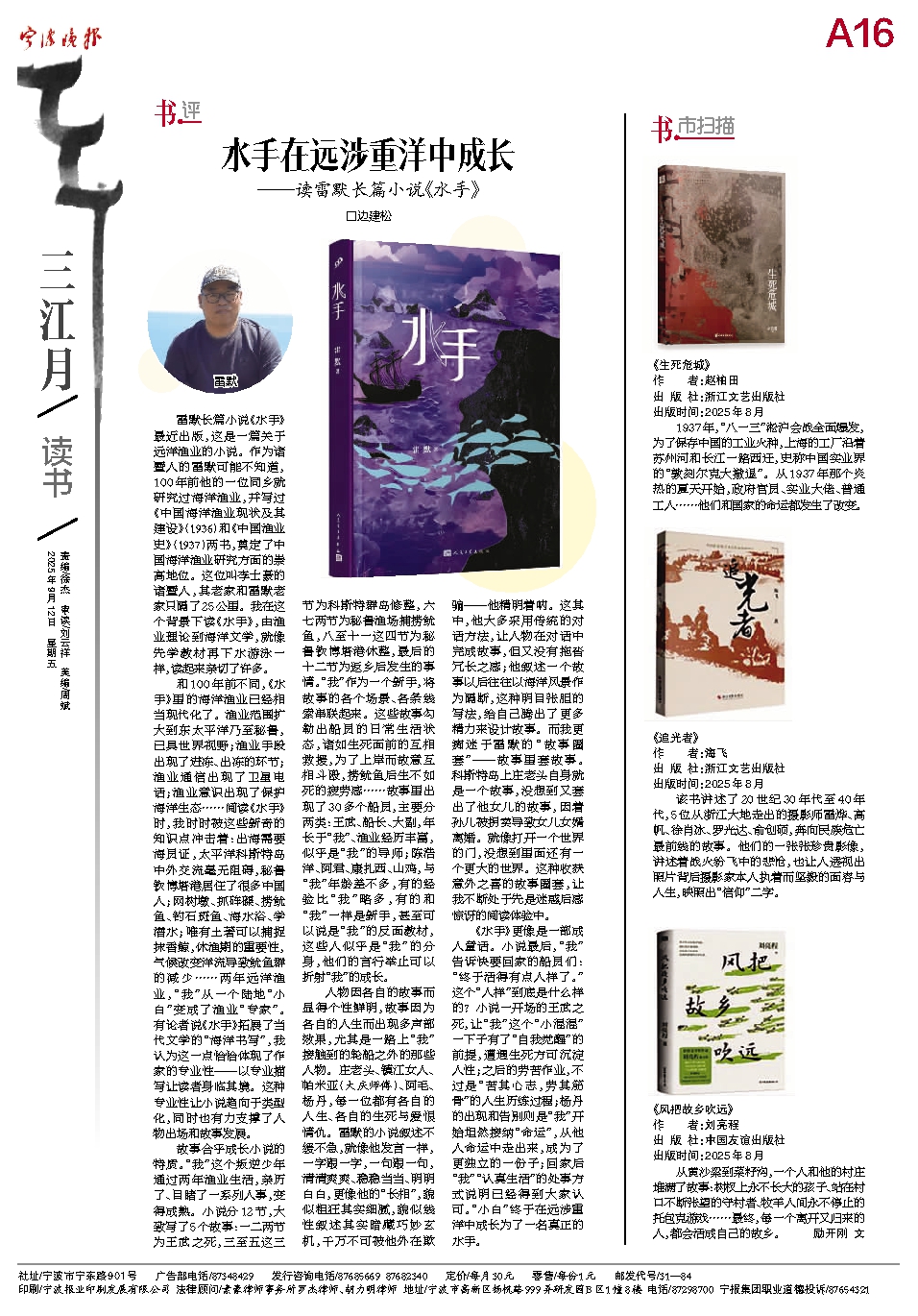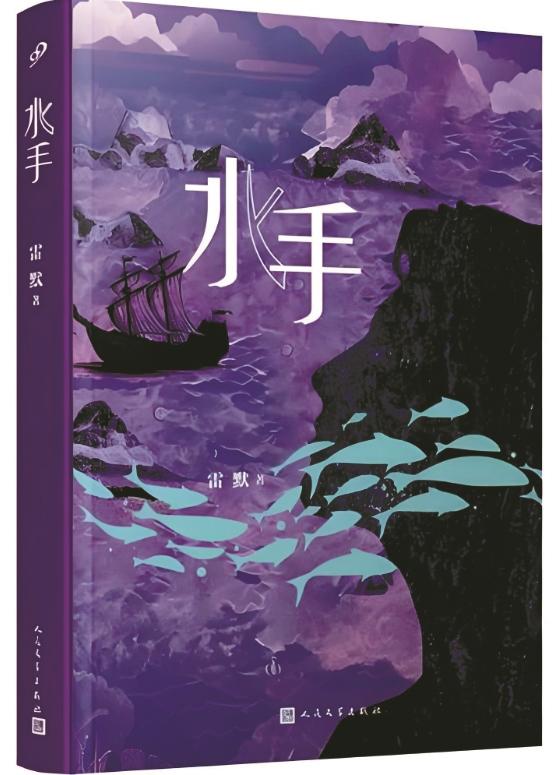雷默长篇小说《水手》最近出版,这是一篇关于远洋渔业的小说。作为诸暨人的雷默可能不知道,100年前他的一位同乡就研究过海洋渔业,并写过《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1936)和《中国渔业史》(1937)两书,奠定了中国海洋渔业研究方面的崇高地位。这位叫李士豪的诸暨人,其老家和雷默老家只隔了25公里。我在这个背景下读《水手》,由渔业理论到海洋文学,就像先学教材再下水游泳一样,读起来亲切了许多。
和100年前不同,《水手》里的海洋渔业已经相当现代化了。渔业范围扩大到东太平洋乃至秘鲁,已具世界视野;渔业手段出现了进冻、出冻的环节;渔业通信出现了卫星电话;渔业意识出现了保护海洋生态……阅读《水手》时,我时时被这些新奇的知识点冲击着:出海需要海员证,太平洋科斯特岛中外交流毫无阻碍,秘鲁钦博塔港居住了很多中国人;网树墩、抓砗磲、捞鱿鱼、钓石斑鱼、海水浴、学潜水;唯有土著可以捕捉抹香鲸,休渔期的重要性,气候改变洋流导致鱿鱼群的减少……两年远洋渔业,“我”从一个陆地“小白”变成了渔业“专家”。有论者说《水手》拓展了当代文学的“海洋书写”,我认为这一点恰恰体现了作家的专业性——以专业描写让读者身临其境。这种专业性让小说趋向于类型化,同时也有力支撑了人物出场和故事发展。
故事合乎成长小说的特质。“我”这个叛逆少年通过两年渔业生活,亲历了、目睹了一系列人事,变得成熟。小说分12节,大致写了5个故事:一二两节为王武之死,三至五这三节为科斯特群岛修整,六七两节为秘鲁渔场捕捞鱿鱼,八至十一这四节为秘鲁钦博塔港休整,最后的十二节为返乡后发生的事情。“我”作为一个新手,将故事的各个场景、各条线索串联起来。这些故事勾勒出船员的日常生活状态,诸如生死面前的互相救援,为了上岸而故意互相斗殴,捞鱿鱼后生不如死的疲劳感……故事里出现了30多个船员,主要分两类:王武、船长、大副,年长于“我”、渔业经历丰富,似乎是“我”的导师;陈浩洋、阿君、康扎西、山鸡,与“我”年龄差不多,有的经验比“我”略多,有的和“我”一样是新手,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反面教材,这些人似乎是“我”的分身,他们的言行举止可以折射“我”的成长。
人物因各自的故事而显得个性鲜明,故事因为各自的人生而出现多声部效果,尤其是一路上“我”接触到的轮船之外的那些人物。庄老头、镇江女人、帕米亚(大庆师傅)、阿毛、杨丹,每一位都有各自的人生、各自的生死与爱恨情仇。雷默的小说叙述不缓不急,就像他发言一样,一字跟一字,一句跟一句,清清爽爽、稳稳当当、明明白白,更像他的“长相”,貌似粗狂其实细腻,貌似线性叙述其实暗藏巧妙玄机,千万不可被他外在欺骗——他精明着呐。这其中,他大多采用传统的对话方法,让人物在对话中完成故事,但又没有拖沓冗长之感;他叙述一个故事以后往往以海洋风景作为隔断,这种明目张胆的写法,给自己腾出了更多精力来设计故事。而我更痴迷于雷默的“故事圈套”——故事里套故事。科斯特岛上庄老头自身就是一个故事,没想到又套出了他女儿的故事,因着孙儿被拐卖导致女儿女婿离婚。就像打开一个世界的门,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这种收获意外之喜的故事圈套,让我不断处于先是迷惑后感惊讶的阅读体验中。
《水手》更像是一部成人童话。小说最后,“我”告诉快要回家的船员们:“终于活得有点人样了。”这个“人样”到底是什么样的?小说一开场的王武之死,让“我”这个“小混混”一下子有了“自我觉醒”的前提,遭遇生死方可沉淀人性;之后的劳苦作业,不过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人生历练过程;杨丹的出现和告别则是“我”开始坦然接纳“命运”,从他人命运中走出来,成为了更独立的一份子;回家后“我”“认真生活”的处事方式说明已经得到大家认可。“小白”终于在远涉重洋中成长为了一名真正的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