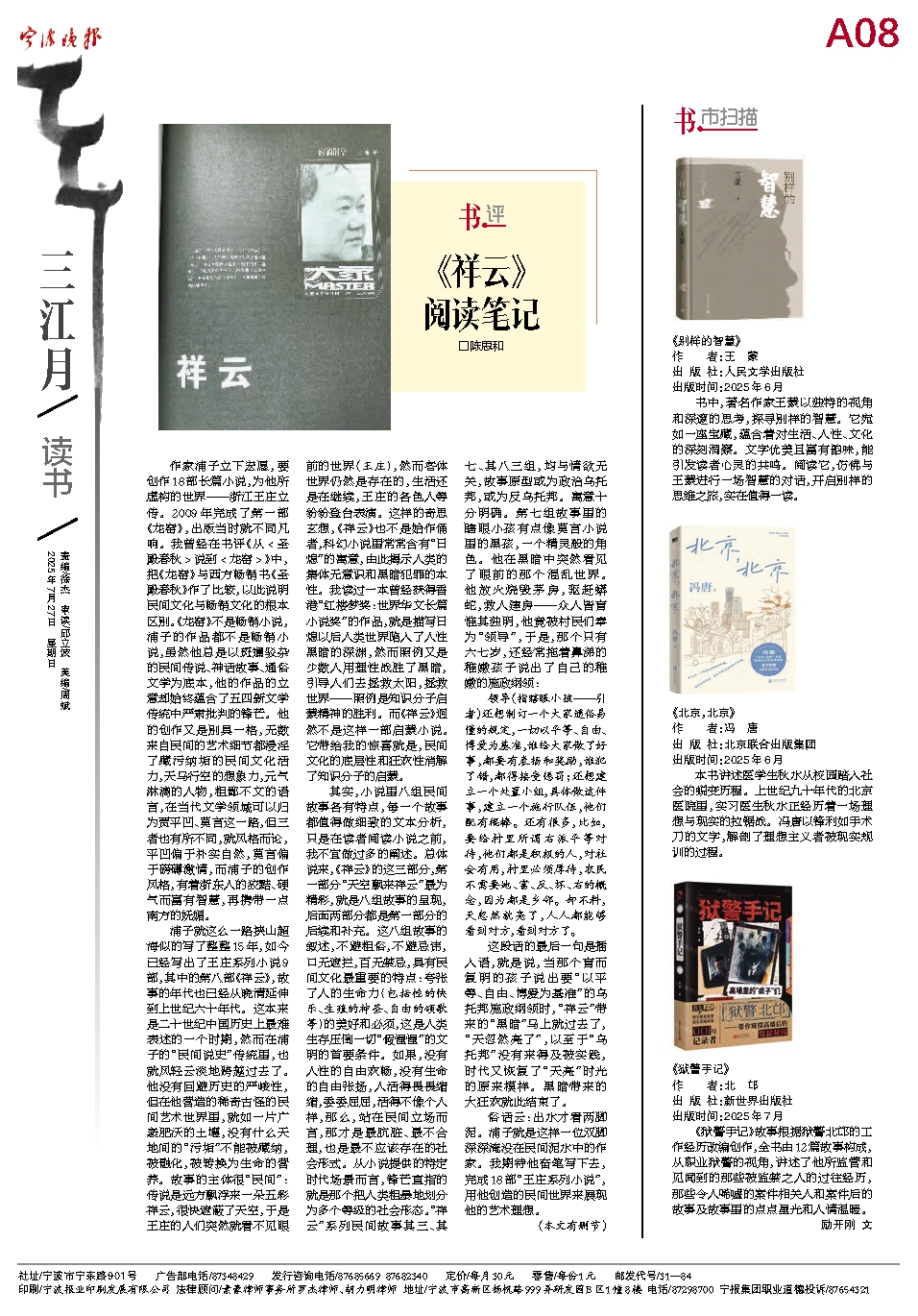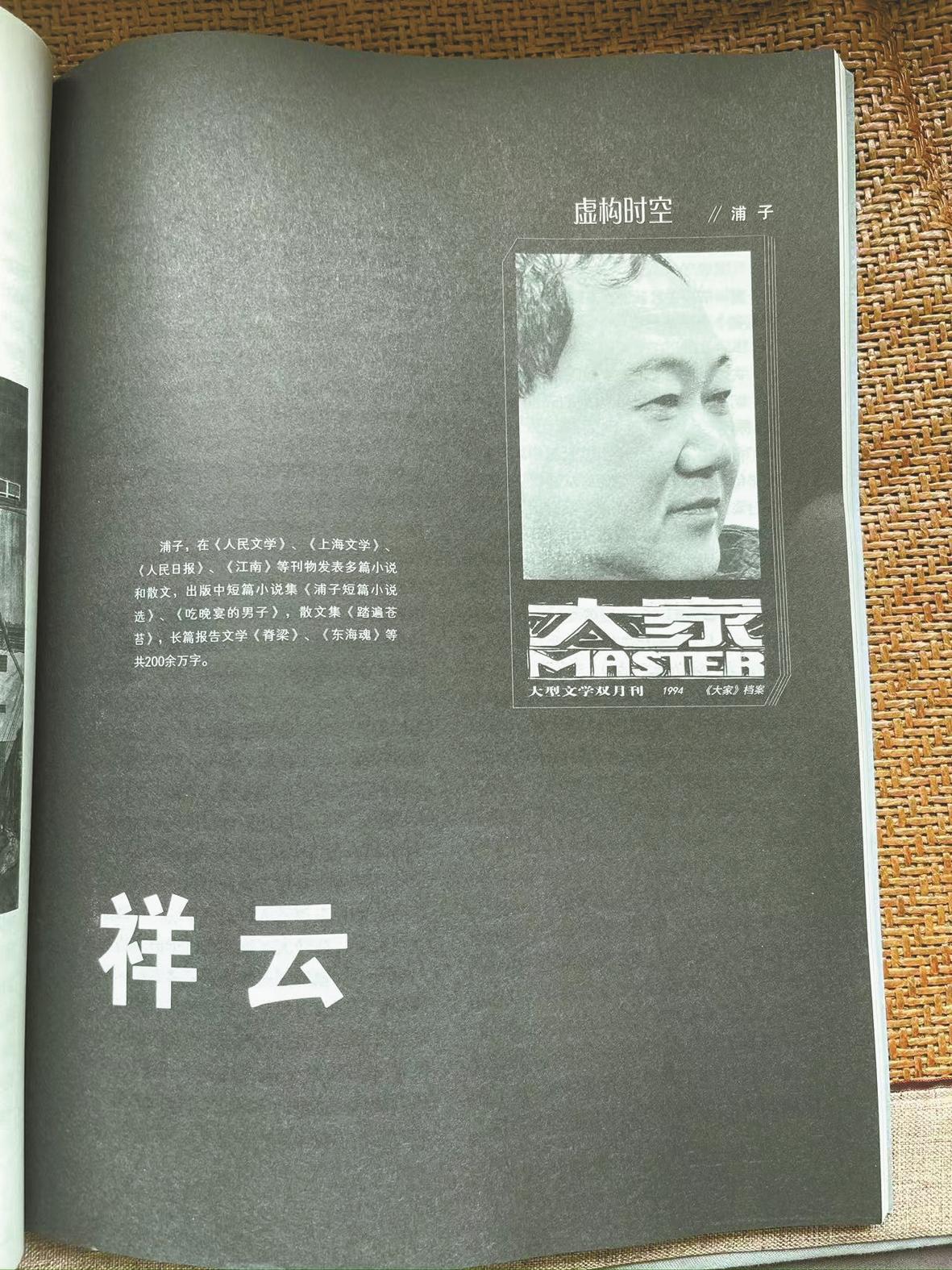□陈思和
作家浦子立下宏愿,要创作18部长篇小说,为他所虚构的世界——浙江王庄立传。2009年完成了第一部《龙窑》,出版当时就不同凡响。我曾经在书评《从﹤圣殿春秋﹥说到﹤龙窑﹥》中,把《龙窑》与西方畅销书《圣殿春秋》作了比较,以此说明民间文化与畅销文化的根本区别。《龙窑》不是畅销小说,浦子的作品都不是畅销小说,虽然他总是以斑斓驳杂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通俗文学为底本,他的作品的立意却始终蕴含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严肃批判的锋芒。他的创作又是别具一格,无数来自民间的艺术细节都浸淫了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活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元气淋漓的人物,粗鄙不文的语言,在当代文学领域可以归为贾平凹、莫言这一路,但三者也有所不同,就风格而论,平凹偏于朴实自然,莫言偏于磅礴激情,而浦子的创作风格,有着浙东人的狡黠、硬气而富有智慧,再携带一点南方的妩媚。
浦子就这么一路挟山超海似的写了整整15年,如今已经写出了王庄系列小说9部,其中的第八部《祥云》,故事的年代也已经从晚清延伸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本来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难表述的一个时期,然而在浦子的“民间说史”传统里,也就风轻云淡地跨越过去了。他没有回避历史的严峻性,但在他营造的稀奇古怪的民间艺术世界里,就如一片广袤肥沃的土壤,没有什么天地间的“污垢”不能被藏纳,被融化,被转换为生命的营养。故事的主体很“民间”:传说是远方飘浮来一朵五彩祥云,很快遮蔽了天空,于是王庄的人们突然就看不见眼前的世界(王庄),然而客体世界仍然是存在的,生活还是在继续,王庄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台表演。这样的奇思玄想,《祥云》也不是始作俑者,科幻小说里常常含有“日熄”的寓意,由此揭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和黑暗犯罪的本性。我读过一本曾经获得香港“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的作品,就是描写日熄以后人类世界陷入了人性黑暗的深渊,然而照例又是少数人用理性战胜了黑暗,引导人们去拯救太阳,拯救世界——照例是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胜利。而《祥云》迥然不是这样一部启蒙小说。它带给我的惊喜就是,民间文化的底层性和狂欢性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启蒙。
其实,小说里八组民间故事各有特点,每一个故事都值得做细致的文本分析,只是在读者阅读小说之前,我不宜做过多的阐述。总体说来,《祥云》的这三部分,第一部分“天空飘来祥云”最为精彩,就是八组故事的呈现,后面两部分都是第一部分的后续和补充。这八组故事的叙述,不避粗俗,不避忌讳,口无遮拦,百无禁忌,具有民间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夸张了人的生命力(包括性的快乐、生殖的神圣、自由的颂歌等)的美好和必须,这是人类生存压倒一切“假惺惺”的文明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人性的自由欢畅,没有生命的自由张扬,人活得畏畏缩缩,委委屈屈,活得不像个人样,那么,站在民间立场而言,那才是最肮脏、最不合理,也是最不应该存在的社会形式。从小说提供的特定时代场景而言,锋芒直指的就是那个把人类粗暴地划分为多个等级的社会形态。“祥云”系列民间故事其三、其七、其八三组,均与情欲无关,故事原型或为政治乌托邦,或为反乌托邦。寓意十分明确。第七组故事里的瞎眼小孩有点像莫言小说里的黑孩,一个精灵般的角色。他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了眼前的那个混乱世界。他放火烧毁茅房,驱赶蟒蛇,救人建房——众人皆盲惟其独明,他竟被村民们奉为“领导”,于是,那个只有六七岁,还经常拖着鼻涕的稚嫩孩子说出了自己的稚嫩的施政纲领:
领导(指瞎眼小孩——引者)还想制订一个大家通俗易懂的规定,一切以平等、自由、博爱为基准,谁给大家做了好事,都要有表扬和奖励,谁犯了错,都得接受惩罚;还想建立一个处置小组,具体做这件事,建立一个施行队伍,他们配有棍棒。还有很多,比如,要给村里所谓右派平等对待,他们都是积极的人,对社会有用,村里必须厚待,农民不需要地、富、反、坏、右的概念,因为都是乡邻。却不料,天忽然就亮了,人人都能够看到对方,看到对方了。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插入语,就是说,当那个盲而复明的孩子说出要“以平等、自由、博爱为基准”的乌托邦施政纲领时,“祥云”带来的“黑暗”马上就过去了,“天忽然亮了”,以至于“乌托邦”没有来得及被实践,时代又恢复了“天亮”时光的原来模样。黑暗带来的大狂欢就此结束了。
俗话云:出水才看两脚泥。浦子就是这样一位双脚深深淹没在民间泥水中的作家。我期待他奋笔写下去,完成18部“王庄系列小说”,用他创造的民间世界来展现他的艺术理想。
(本文有删节)